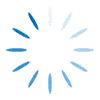1970年6月17日 14:00|瀋阳,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」主席府
王明坐在那张曾经属于东北局的办公桌后面,感觉自己像一个被遗忘在舞台上的木偶。
窗外的瀋阳阳光灿烂,街道上偶尔有行人走过。如果不是隔几条街就能看到的苏军检查站,如果不是空气中偶尔飘来的消毒水味道,这座城市看起来几乎恢復了正常。
但他知道,这一切都是假象。
「主席同志,」秘书推门进来,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,「苏联顾问团的伊万诺夫将军来了。」
王明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。「请他进来。」
伊万诺夫是驻瀋阳的苏军政治顾问,名义上是「协助」新政权建设,实际上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真正主人。每週他都会来一次,名为「汇报工作」,实为下达命令。
门开了,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军官走进来。他穿着笔挺的苏军制服,胸前掛满勋章,灰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。
「王明同志,」他用生硬的中文说,「您好。」
「伊万诺夫将军。」王明站起身,微微欠身。这个动作让他感到一阵耻辱,但他已经习惯了。
伊万诺夫没有客套,直接在沙发上坐下,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。
「莫斯科对最近的『治安形势』很不满意。」他说,手指敲着文件,「上个月,在你们管辖的区域内,发生了一百三十七起『恐怖袭击』。二十三名苏军士兵阵亡,四十七人受伤。另外,还有十一名你们的地方官员被暗杀。」
王明的脸色变了。「将军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游击队藏在民间,很难分辨……」
「这不是藉口。」伊万诺夫打断他,语气冰冷,「莫斯科认为,问题出在你们的政策太软弱。你们对那些同情游击队的人太宽容了。」
伊万诺夫站起身,走到窗前,背对着王明。
「连坐制。」他说,「任何村庄如果窝藏游击队,全村男性处决,女性和儿童送往劳动营。任何城市如果发生暗杀事件,随机抓捕一百名『嫌疑人』公开处决。」
王明的脸色变得苍白。「将军,这……这会激起更大的反抗……」
「这是命令。」伊万诺夫转过身,目光锐利,「不是建议。」
他走向门口,又停下脚步,回头看了王明一眼。
「王明同志,我提醒您一件事:您之所以坐在这把椅子上,是因为莫斯科需要一个中国人的面孔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您不可替代。中国有很多人愿意合作,您明白吗?」
王明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,浑身发抖。
他想起了三十年前,自己在莫斯科的日子。那时候他是共產国际的宠儿,是中国革命的「理论权威」,意气风发,以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到中国,领导那场伟大的革命。
现在他回来了。但不是作为领袖,而是作为傀儡。
他走到窗前,望着外面的街道。一队苏军士兵正在走过,他们的军靴在柏油路上踏出整齐的声响。路边,几个中国人低着头快步走过,没有人敢抬头看那些士兵。
这就是他「解放」的中国。
王明闭上眼睛,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口慢慢破碎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那天晚上,王明做了一个梦。
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延安,回到了1938年。窑洞里,毛泽东正靠在土炕上,手里夹着一支烟,瞇着眼睛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「国际路线」。
「泽东同志,」梦中的他说,「共產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,我们必须服从……」
毛泽东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他,嘴角掛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那微笑里有轻蔑,有怜悯,也有某种更深沉的东西。
「王明啊王明,」毛泽东终于开口,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「你这辈子,就不明白一个道理。」
「中国的事情,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。」
梦境碎裂。王明猛地坐起来,发现自己浑身是汗。
窗外,瀋阳的夜空被探照灯割裂成一道道光柱。远处隐隐传来枪声——也许是又一起「恐怖袭击」,也许只是苏军在夜间巡逻时对着影子开枪。
他躺回床上,盯着天花板,一夜无眠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0年6月20日 黎明|河北,太行山区
张秀英已经在山里躲了七个月了。
她今年四十二岁,曾经是石家庄纺织厂的女工,有一个丈夫和两个孩子。去年十一月,苏军佔领石家庄后,她的丈夫因为「私藏武器」——其实只是一把生锈的菜刀——被当街枪毙。她带着两个孩子逃进了太行山,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。
现在,她的大儿子已经成了一名游击队员,十六岁,会用步枪、会埋地雷、会在夜里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。小女儿十二岁,在山洞里的「流动学校」上课,学认字、学算术、学唱那些被禁止的歌。
而她自己,成了游击队的炊事员和护理员。
「娘,」大儿子李建国从外面鑽进山洞,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,「队长说今晚有行动。」
张秀英正在用野菜和小米熬粥。她的手顿了一下,但没有抬头。
「打苏修的运输队。」李建国蹲到她身边,压低声音,「情报说,今晚有一队卡车要从井陘经过,运的是弹药。队长让我跟着去。」
她抬起头,看着儿子的脸。那张脸还带着少年的稚气,但眼睛里已经有了某种她不认识的东西——那是见过血、杀过人之后才会有的东西。
「建国,」她的声音有些发涩,「你爹死的时候,你才十五岁。我答应过他,要把你们兄妹养大成人。」
「让我说完。」张秀英打断他,「我不是要拦你。我知道拦不住。你爹的仇要报,国家的仇也要报。但是……」
她伸出手,抚摸儿子的脸颊。那脸颊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绒毛,不再是她记忆中那个软软的、滑滑的婴儿脸蛋了。
「但是,你要答应我,活着回来。」
他站起身,从墙角拿起那支缴获来的莫辛纳甘步枪,走向洞口。
「娘,」他停下脚步,回头看了一眼,「粥熬好了给小妹留着,我回来再吃。」
然后他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。
张秀英独自坐在山洞里,听着洞外的风声和偶尔传来的鸟鸣。火堆上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,散发出一股清淡的香气。
她没有哭。这七个月来,她已经哭乾了眼泪。丈夫死的时候她哭过,逃进山里的时候她哭过,第一次给伤员包扎伤口、看着那些年轻人在她面前咽气的时候她也哭过。
她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——不是向任何神明,而是向那些已经死去的人——她的丈夫,她的父母,她的邻居,还有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、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千千万万的人。
「保佑他。」她轻声说,「保佑他活着回来。」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那天晚上的伏击战打了不到二十分鐘。
游击队埋伏在公路旁的山坡上,等苏军的运输车队进入射程后,先用地雷炸毁了头车和尾车,然后居高临下开火。黑暗中,苏军士兵慌乱地从卡车上跳下来,胡乱还击,但他们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。
等护航的装甲车赶来增援时,游击队已经带着缴获的弹药消失在夜色中。
第二天黎明,一个浑身是血的游击队员爬回了营地,带来了消息:李建国在撤退时中弹了,子弹穿过他的腹部。他让战友们先走,自己留下来掩护。
「他说……」那个游击队员的声音颤抖着,「他说让我告诉他娘,他对不起她,没能活着回来。」
张秀英听完这句话,没有哭。
她只是站起身,走到洞口,望着远处连绵的太行山脉。晨光正在山峦间升起,把天边染成一片金红色。
「小妹,」她说,声音平静得出奇,「过来。」
十二岁的李小妹从山洞深处走出来,怯生生地看着母亲。
「你哥不回来了。」张秀英说,「从今天起,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了。」
李小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「娘……」
「不许哭。」张秀英的声音严厉了,「你哥是为国家死的,是英雄,不是让人哭的。」
她蹲下身,平视女儿的眼睛。
「小妹,你记住,你哥死的时候才十六岁。他没能看到苏修被赶走的那一天,但你要替他看到。你要好好活着,好好学习,将来……将来等这场仗打完了,你要告诉你的孩子、你孩子的孩子,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什么,告诉他们你哥是怎么死的。」
「我记住了,娘。」李小妹抽噎着说。
张秀英站起身,拍了拍女儿的头。
她转身走回山洞,继续熬她的粥。炉火映照着她的脸庞,那张脸上没有眼泪,只有一种石头般的坚硬。
后来,有人说张秀英疯了——因为她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笑过,再也没有哭过,整个人像一具行走的躯壳。
但也有人说,她只是把所有的悲伤和愤怒都压进了心底,变成了一块烧红的铁,等待着有一天把它锻造成一把刺向敌人的刀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0年7月4日|华盛顿,美国独立纪念日
「中国:一场被遗忘的战争」
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 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 报导
今天是美国独立194週年纪念日。当华盛顿的市民们在国家广场上观看烟火表演、庆祝自由与独立的时候,在地球的另一端,另一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战争正在继续——而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。
九个月前,苏联对中国发动了突然袭击。这场战争以核打击开始,以北京的陷落告一段落。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首都的保卫战中身亡,残存的政府撤退到了西南山区。
在官方的叙述中,这场战争已经「结束」了。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控制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,而「自由中国」——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——蜷缩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和广东的部分地区,苟延残喘。
本记者最近秘密进入中国境内,在华北的游击区度过了三週时间。我看到的景象与官方叙述大相径庭:在太行山的密林里,在河北的平原村庄中,在每一条被炸毁又修復、修復又炸毁的公路旁,一场无声的战争正在进行。
游击队员们告诉我,他们不指望能打败苏联的正规军。他们的目标更简单,也更残酷:让佔领者一天都不得安寧,让每一个苏联士兵在踏上中国土地的每一刻都感到恐惧,让这场佔领的代价高到莫斯科无法承受。
「我们像水一样,」一位游击队指挥员对我说,「你可以用火烧开水,但你烧不乾大海。」
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越南。想起了那些在丛林中与我们的军队周旋的越共游击队。想起了一个超级大国是如何在一个小国的顽强抵抗面前陷入泥潭的。
苏联正在重蹈我们在越南的覆辙吗?
也许时间会给出答案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:这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。而当我们在烟火照耀下庆祝自由的时候,也许应该想一想——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,有些人正在为同样的东西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0年8月15日 深夜|重庆,周恩来办公室
周恩来放下手中的《纽约时报》剪报,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
这篇报导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据说尼克森总统亲自读了这篇文章,还在白宫的内部会议上提到了它。美国国会里,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加大对「自由中国」的援助。
但这些对他来说,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「总理,」秘书钱嘉东轻轻敲门,「邓小平同志到了。」
门开了,一个身材矮小但精神矍鑠的男人走了进来。邓小平比周恩来小六岁,但这几年的颠沛流离让他看起来老了许多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,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,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,透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光芒。
「恩来,」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,「你找我?」
「小平,」周恩来倒了两杯茶,推了一杯过去,「我想和你谈谈……将来的事。」
「将来?」邓小平端起茶杯,「你是说战争结束之后?」
「不只是战争。」周恩来的声音低沉,「我是说……我之后。」
邓小平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放下茶杯,直视周恩来的眼睛。
「恩来,你身体怎么了?」
「前列腺有些问题。」他说,「医生说需要进一步检查,但……」他苦笑了一下,「你知道现在的条件,进一步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名堂。」
「那你就更应该保重身体。」邓小平的语气严厉了,「恩来,你是我们的主心骨。你要是倒下了……」
「所以我才找你谈这件事。」周恩来打断他,「小平,我直说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,这个担子,你要挑起来。」
房间里只有掛鐘的滴答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虫鸣。
「恩来,」他终于开口,声音沙哑,「你知道我的情况。文革的时候,我被打成『党内第二号走资派』。现在虽然恢復了工作,但很多人……很多人还对我有看法。」
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」周恩来摇头,「主席已经不在了,文革也已经结束了。现在重要的是,怎么把这场仗打下去,怎么把这个国家撑下去。」
「小平,我告诉你我的判断。这场战争,我们赢不了——至少在军事上赢不了。苏联太强大了,我们的差距太大了。但是……」
「但是,苏联也赢不了。他们可以佔领我们的城市,但他们佔领不了我们的人心。只要我们坚持抵抗,只要这团火不灭,他们就永远无法真正征服中国。」
「最终……」周恩来沉吟了一下,「最终会是一场消耗战。比的是谁能撑得更久。苏联的经济有问题,他们的体制有问题,他们和美国的竞争也在消耗他们的力量。如果我们能撑住十年、二十年,说不定……说不定会有转机。」
「十年、二十年。」邓小平苦笑,「恩来,我们还能撑那么久吗?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周恩来坦率地说,「但我知道,只要还有一口气,就不能放弃。这是主席留给我们的遗言,也是我们对死去的那些人的责任。」
他走回座位,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。
「这是我拟的一个方案,关于长期抵抗的战略规划。游击区的建设、敌佔区的渗透、国际统一战线的经营……我想让你过目一下,提提意见。」
邓小平接过文件,却没有立刻打开。
「恩来,」他说,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。」
「这场仗……值得吗?」
「我的意思是,」邓小平的声音低沉,「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。北方的几千万同胞在苏联人的铁蹄下受苦。如果当初我们……如果当初我们选择谈判,选择妥协,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一切?」
「小平,这个问题,我也问过自己无数次。」他的声音疲惫而苍凉,「如果当初不抵抗,如果当初接受苏联的条件,是不是可以少死很多人?也许可以。但是……」
「但是,那样的中国,还是中国吗?一个跪着的中国,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,一个丧失了尊严和意志的中国——那还值得存在吗?」
他看着邓小平,目光灼灼。
「主席说过,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,打不垮的。这句话,不只是一句口号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来的生存之道。秦始皇杀不完六国的遗民,蒙古人杀不完南宋的军民,日本人杀不完中华的儿女。苏联人……也杀不完。」
「只要我们还在抵抗,中国就没有亡。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我们是中国人,记得我们为什么而战,这团火就不会灭。」
「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胜利。也许下一代人也看不到。但总有一天……总有一天,这片土地会重新属于中国人。那一天,我们这些人的名字,会被刻在歷史的丰碑上。」
「我明白了。」他终于说,声音坚定,「恩来,你放心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,我就会把这面旗扛下去。」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